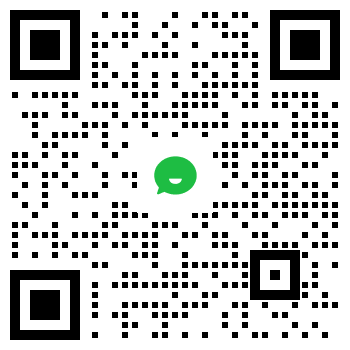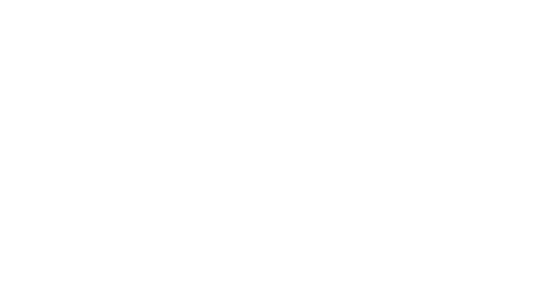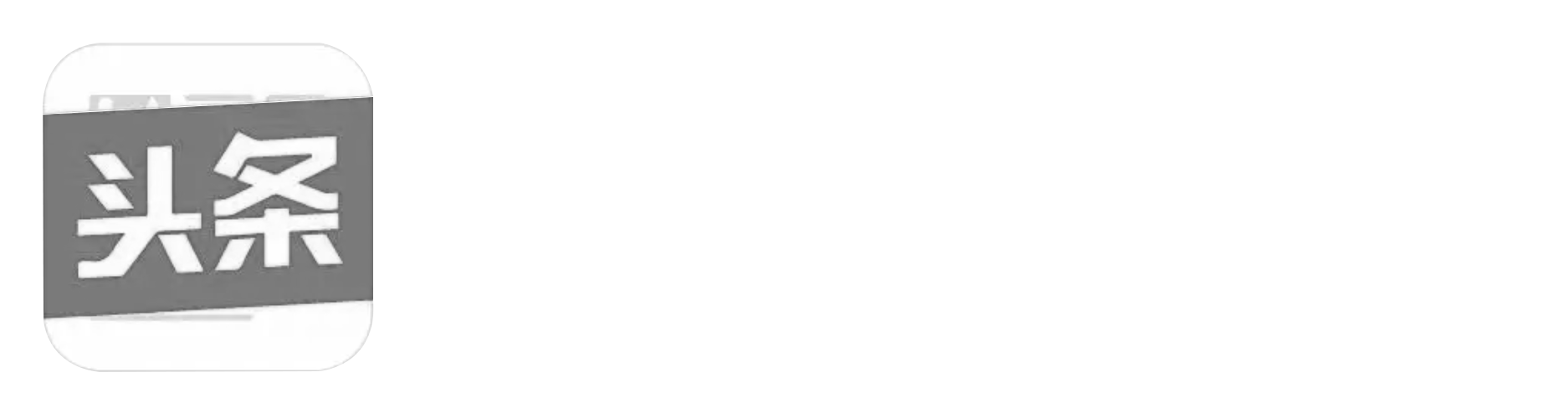圍堵升級。
美國針對全球貿易的“大網”正在逐漸收攏。
上周,特朗普政府向包括日、韓及東盟在內的14國發出信函,宣布自8月1日起大幅提升關稅,并明確警告將打擊“為逃避高額關稅而轉運的貨物”。這一行動,讓曾被視為規避關稅“安全港”的東南亞,瞬間成為風暴眼。
從華盛頓的視角來看,其行動的理據清晰地呈現在貿易數據中。自2018年以來,越南對美出口額激增的同時,其從中國的進口額也幾乎同步增長。
另有數據顯示在2017年至2024年間,中國在美國總進口中的份額下降了8.1個百分點,而越南和墨西哥的份額則顯著上升。這被美方解讀為貿易“重新路由”的確鑿證據,也正是此次精準打擊的靶心。
越南與美國達成的初步協議極具代表性:經由越南轉運的商品將面臨40%的高額關稅,其中鋰電池赫然在列。
印尼則同意對本國對美出口商品征收19%關稅,但也附加了針對轉運的懲罰性條款。
其他東盟國家面臨的潛在稅率從32%至40%不等,已接近轉運懲罰的水平。
然而,一個關鍵問題是,美國似乎并未仔細甄別“轉口貿易”與“綠地投資”的區別。近年來,中國企業的東南亞布局已遠超簡單的產品出口。
寧德時代在印尼的電池廠、國軒高科在越南的工廠、億緯鋰能在馬來西亞的基地,其投資模式更接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(IMF)所定義的“綠地投資”:
不僅轉移組裝線,更將相當一部分零部件制造、甚至上游材料等高附加值環節真實地部署到當地。
包括星源材質、新宙邦、龍蟠科技等在內的鋰電核心材料廠商,亦在東南亞落地、規劃了產能布局。
這本應是滿足東道國要求、規避“轉運”嫌疑的深度本土化戰略。但美國發出的信號實在模糊:
以電池產業為例,一個生動的場景是:一個在中國生產的電芯,運到越南僅作最后的電池包組裝后出口,這是否會被視為轉運?
更進一步,如果電芯本身在越南生產,采用了越南當地的正極、隔膜和電解液,但其關鍵的負極材料和集流體依然從中國進口,那么這個產品的原產地究竟是哪里?
以增值程度為核心的判斷標準,其具體的計算方式又是什么?增值率需要達到多少才能被認定為本地生產?
懸而未決的“轉運”定義與原產地規則,讓這些重資產投資的前景同樣充滿了高度不確定性。
不只是關稅升級
要理解當前的風險,必須認識到這并非一次戰術性升級(將對等關稅與針對特定行業、國家的精準打擊相結合),而是一場全球貿易格局的深刻變革。
多家機構認為,這是自1930年《斯穆特-霍利關稅法》以來最大規模的關稅提升。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測算,美國最終落地的平均有效關稅率將超過20%,為1910年來最高。
其背后,根植于特朗普2.0政府三大核心理念的混合驅動,使其比單一動機的保護主義更具持久性。
首先,是對抗中國的國家主導型產業政策。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報告直言不諱,對中國電動汽車、電池和太陽能等“新三樣”加征關稅,旨在反擊其非市場行為。
其次,是重振國內制造業的“經濟民族主義”,關稅與“大而美”法案等國內產業政策形成互補,旨在激勵企業將供應鏈遷回美國。
最后,是對貿易逆差的零和博弈式執念。直接將美國定義為“損失”和對方“勝利”,實際上是將國際貿易視為一場競爭而非合作。
這種做法公然背離了WTO“最惠國待遇”的基本原則,即要求對所有貿易伙伴一視同仁,被中國外交部指為“觸及多邊貿易體系的底線”。
此外,財政需求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。在“大而美法案”減稅幅度遠大于減支的背景下,關稅成為了籌集財政收入的重要手段。
但對美國自身而言,代價或將同樣巨大。耶魯大學的預測顯示,關稅將導致物價上漲2.1%,相當于每戶家庭損失2800美元,并導致實際GDP永久性地縮小0.5%。
在全球層面,一個更深遠的變化已經發生。地緣政治現實,正在加速全球供應鏈從過去的“效率驅動”轉向“安全和陣營驅動”。
數據顯示,地緣政治上“親美”與“親華”兩大集團間的貿易增速,已比集團內部貿易增速低了近5個百分點。中國企業面臨的,是一個日益碎片化的全球格局。
滯后的沖擊波:從市場疲勞到產業陣痛
盡管關稅警報頻傳,金融市場的反應卻異常平靜,美元溫和回落,美股保持堅挺。摩根大通的報告將此歸因于市場的“關稅疲勞”,以及企業通過提前囤積庫存、調整采購地等戰術手段進行的短期緩沖。
但這份平靜具有欺騙性。據其預計,關稅的滯后影響預計將在今年第三、四季度庫存耗盡后完全顯性化。屆時,成本壓力將直接傳導至全球企業的利潤。
另有分析師警告,關稅帶來的成本上升將抑制美國這一最大市場的長期需求,并向上游的全球供應鏈傳導。
在關稅尚未實施前,美國部分必需消費品價格已在一季度上漲,而對于非必需品,問題不僅是漲價,更是需求會否因此消失。
這場沖擊波對中國鋰電產業的打擊尤為精準且沉重。美國是中國鋰電池無可爭議的第一大出口市場,2024年出口額超過150億美元,占中國鋰電池出口總額高達25%,其后才是德國和韓國等國家。
在最悲觀的假設下,如果這部分出口全部被替代,意味著中國將失去一個價值超150億美元的龐大市場。
而這場外部沖擊,恰好發生在中國國內鋰電產業一個較為脆弱的時刻。
供需錯配帶來的價格內卷曠日持久,目前,旨在化解產能過剩的“反內卷”(實為供給側改革)尚處于信號釋放的初期,但國內需求側的刺激政策卻顯得乏力。
在當前相對逼仄的政策空間下,“以舊換新”政策的提振效應可能在下半年逐步減退,而市場又缺乏強勁的同步復蘇信號。
在這種背景下,出口將帶來的“優質需求”的萎縮,可能導致“單純依靠去產能”的改革陷入供給與需求同時下行的困境。已有電池企業表示,“儲能電池若不出口,在國內還是虧損”,這正是這種困境最直白的體現。
與此同時,中美在新能源領域的博弈信號也在不斷升級。在圍繞關稅的兩輪談判(5月10日于日內瓦,6月上旬于倫敦)后,雙方暫時設定的對等關稅“暫停鍵”將截止到8月12日。
與此同時,中國在7月15日正式調整發布了《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》,在電池技術方面,新增了“電池用磷酸鐵鋰制備技術”、“電池用磷酸錳鐵鋰制備技術”等三條控制要點。
值得注意的是,在征求意見稿中,相關技術主要針對高強度、高壓實類的磷酸鐵鋰和快充類磷酸錳鐵鋰等下一代產品和技術;而在終版中,對磷酸鐵鋰的參數范圍限制,已縮窄至更接近量產應用的產品。不過,被列為“限制性”而非“禁止性”條目,意味著經審批后仍可出口。
此舉被視為一種精準且不屈服的技術博弈姿態。
從“轉口”走向“扎根”
面對徹底改變的游戲規則,中國企業的全球化戰略正在被迫加速、徹底進化。從過去的“借道出海”,升級為“深度扎根”。
這意味著從“貿易轉運”(trade rerouting)向IMF所稱的“貿易再配置”(trade reallocation)的結構性轉變。
榮鼎集團的報告證實了這一趨勢:比亞迪、上汽、奇瑞等車企正在顯著加快在歐洲、墨西哥、巴西等地的本地化生產設施建設。比亞迪在東南亞提出的“即時采購”的模式,更是從側面印證了其構建本地化供應商生態的戰略意圖。中國的電池制造商在海外布局時,同樣傾向于將整個供應鏈一同帶出。
然而,核心的困境在于,這種“深度本土化”的“正確”戰略,是否足以應對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。
即便企業進行了真實的綠地投資,滿足了東道國對增加值和就業的全部要求,但只要其背后是中國資本,且處于電動汽車、電池這樣的敏感行業,就始終面臨風險。
針對“新三樣”的圍堵,或許總會以不同形式出現。如果反轉運關稅不足以達成目標,更嚴苛的原產地規則、對東道國的直接施壓、乃至新的非關稅壁壘都可能接踵而至。
這場變革的本質,是企業全球布局的底層邏輯已從過去以勞動力和物流成本為核心的“效率模型”,徹底轉向了以關稅和地緣政治風險為核心的“合規與安全模型”。
對于致力于全球化的中國企業而言,這不僅僅是一個需要支付更高稅率的時期,而是一個需要在一個反對自由貿易的、碎片化的全球格局中,為應對隨時可能變化的規則而不斷調整身位的,充滿挑戰的新時代。
特別聲明:本網站轉載的所有內容,均已署名來源與作者,版權歸原作者所有,若有侵權,請聯系我們刪除。凡來源注明低碳網的內容為低碳網原創,轉載需注明來源。
-
1
-
2
-
3
-
4
-
5
-
6
-
7
-
8
-
9